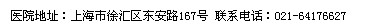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葡萄膜炎 > 葡萄膜炎常识 > 免疫学视角丨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的免疫微
免疫学视角丨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的免疫微
导读
葡萄膜黑色素瘤(UM)是起源于眼睛葡萄膜的黑色素瘤。在美国,UM发病率约为5/,,欧洲约为2~8/,。尽管UM与皮肤黑色素瘤共享胚胎来源,但是二者的生物学行为,流行病学,预后特征和分子谱不同。本文主要探讨转移性UM的免疫微环境。
葡萄膜黑色素瘤(UM)风险因素包括巨大肿瘤,上皮样细胞,虹膜外扩散,染色体3缺失以及染色体8q扩增。超过80%的UM患者在诊断后10年内发生转移。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肝脏,其次是肺和骨骼。
肝转移是临床过程和生存的主要决定因素。据报道,肝转移发展后,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6-12个月。肝脏中的免疫细胞具有不同的功能,进入肝脏的循环肿瘤细胞(CTC)会与独特的免疫系统“相遇”。肝脏免疫系统与癌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肿瘤微环境。
原发性UM的免疫微环境
眼睛是一种具有免疫特权的器官,它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可以用来防御损害视力的不可控炎症。眼睛中免疫应答发展的解剖学限制包括没有阻碍淋巴细胞与眼睛之间“交流”的淋巴管。进入眼睛的免疫细胞会遇到免疫抑制因子,如TGF-β,αMSH,视黄酸(RA)和IDO。这些因子可能抑制T细胞增殖和效应功能,并诱导免疫抑制性Treg细胞。一般地,富含淋巴细胞的肿瘤微环境通常表明预后良好。然而,矛盾的是,UM中的高密度免疫细胞与不良预后因素有关。相较于具有二倍体3的原发性UM,具有单倍体3的原发性UM与更强的炎症反应以及大量免疫细胞浸润相关。免疫细胞浸润更频繁地发生于上皮样细胞型UM。巨噬细胞数量增加与上皮样肿瘤细胞(p=0.),高色素沉着(p=0.)和高微血管密度(p=0.)有关。随着巨噬细胞数量增加,10年黑色素瘤特异性死亡率增加(低数量0.10vs.高数量0.57,p=0.2)。据报道,趋化因子,CCL17和CCL22将Treg细胞募集至肿瘤。肿瘤诱导的CCL17和CCL22不仅吸引促瘤巨噬细胞,还促进它们的生存和M2极化。
虽然UM细胞拥有肿瘤相关抗原,肿瘤浸润性CD4+和CD8+细胞存在于原发性UM中,但是Treg细胞也存在于肿瘤中。一项研究表明,原发性UM中CD4+,叉头框蛋白P3(FOXP3)+Treg细胞频率与全身转移发展有关。肿瘤中的Treg细胞和环氧化酶-2与不良预后相关。就原发性UM中NK细胞的作用而言,HLA-I类分子下调使得肿瘤更易受NK细胞介导的溶解影响。然而,尽管NKG2D配体(MIC-A和B)由50%的原发性UM表达,但转移性UM并未表达这些配体,这表明转移性UM可能不受NK细胞控制。
原发性UM炎性细胞浸润机制以及临床结果相互矛盾的原因仍存疑。大量证据表明,肿瘤微环境干扰有助于肿瘤细胞调节炎症反应。癌细胞与固有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并且使获得性T细胞应答由TH1型向TH2型倾斜。癌细胞也可以使巨噬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表型倾斜至2型分化,并将髓源性抑制细胞和Treg细胞吸引至肿瘤部位。UM细胞可以利用这些免疫细胞进行存活并逃避免疫攻击。UM细胞离开眼睛时可能已经诱导了耐受。肝脏中的免疫调节微环境可以进一步保护逃逸的UM细胞免受全身免疫监视。
肝脏转移机制
肝脏转移发展机制仍然具有很强的推测性。多种因素能够促进肝脏中UM细胞转移和生长,假定机制如下:
1肝脏血液循环缓慢
肝血窦位于动脉(肝动脉)和静脉(门静脉)血液汇合处,混合来自肝动脉中富含氧气的血液和来自门静脉的富含营养物质的血液。它们是一种类似毛细血管的血管,具有窗孔,不连续的内皮细胞。肝血窦中的缓慢血流使肝细胞和致病分子之间的接触最大化,以在循环之前进行过滤。缓慢而曲折的窦血流可以捕获肝脏中的UM细胞。
2
化学诱导剂与其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肝脏产生的趋化因子可能吸引UM入肝脏,并与其表面上的趋化因子受体相互作用。典型的例子为CXCR4与其配体CXCL12之间的相互作用。原发性UM细胞系表达CXCR4。趋化因子相关肝向性的另一种解释是肝脏趋化因子受体缺失。一旦黑色素瘤细胞转移至肝脏,肝脏中UM细胞滞留可能不仅与趋向肝脏的趋化因子梯度相关,还与趋化因子受体缺失有关。另外一个例子为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HGF)c-Met。表达c-Met的UM细胞与肝脏中产生的HGF相互作用。转移的原发性UM细胞较未转移肿瘤具有更高水平的c-Met表达。原发性UM标本中c-Met表达显著增加随后肝转移风险。
3
肝脏中富含生长因子
胰岛样生长因子1(IGF-1)在肿瘤转化,维持恶性表型,促进细胞生长和预防细胞凋亡方面起主要作用。它主要产生自肝脏。UM肝转移样本中可检测到IGF-1受体(IGF-1R)高表达。相关研究表明,肿瘤表面IGF-1R表达与UM进展相关。此外,HGF可以促进肝脏中表达c-Met的UM细胞生长。
4
染色体与遗传异常
相较于皮肤黑色素瘤(CM),UM具有独特的异常遗传特征。BRCA1相关蛋白1(BAP1)突变经常发生于转移性UM。UM细胞中BAP1突变可能导致肝脏向性。然而,这可能是肝脏向性的过简描述。多倍染色体8q是转移性UM的一种常见特征。
5
粘附分子在血窦中表达
血管粘附分子1(VCAM-1)表达于窦状内皮细胞,可能捕获缓慢血流中的癌细胞。炎症条件下,VCAM-1表达于内皮细胞并介导各种白细胞亚群以及癌细胞波动和粘附,以招募和沉降血流中的细胞。动物模型中,部分肝切除诱导了炎性细胞因子(如TNF-α,IL-1β和IL-6)以及VCAM-1表达,并促进了肝转移。内皮细胞VCAM-1表达表明人恶性黑素瘤细胞的粘附。
6
肝脏中富含血管生成因子
肝脏中富含IL-8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它们可促进肝脏微环境中肿瘤血管的生成。肿瘤基质中的肝星状细胞(HSC)主要产生IL-8,并应用抗体中和IL-8以显著降低血管生成效应。IL-8还通过NFkB激活诱导内皮细胞表面VEGFR2和VEGF的表达,并介导血管内皮自分泌和旁分泌刺激。
7
免疫调节微环境
肝脏是一种免疫调节器官,复杂的免疫微环境可以促进肝脏中肿瘤转移和生长。
8
肝免疫微环境的免疫学方面
肝脏具有复杂的免疫微环境。它不断暴露于外来病原体,如食物抗原和低水平内毒素,这种外来病原体多数来源于肠道。局部免疫系统必须不断提供安全机制来消除这些病理抗原和毒素,同时保持对饮食抗原的耐受性。此外,肝脏易受肠粘膜内感染性病原体的侵袭,肝脏免疫系统必须清除这些感染性病原体,以保护宿主免受全身性感染。因此,肝脏免疫力存在于耐受必需元素和防御病理因素之间的微妙平衡中。
肝脏中的居留细胞(非游走细胞)
免疫微环境稳态受肝脏中各种居留非免疫细胞和免疫细胞的严格控制。肝脏中存在多种居留细胞,如肝窦内皮细胞(LSEC),Kupffer细胞(KC),HSC和肝细胞。
1LSEC
LSEC通过窦周隙分离窦腔中的肝细胞和血液。LSEC无基底膜,这种结构使得血液和肝细胞之间进行快速分子交换。HSC滞留于窦周隙,淋巴收集自该间隙,并流入淋巴管,淋巴管通过门管区进入引流淋巴结。LSEC具有胞吞和吞噬能力,并且作为APC呈递抗原。LSEC在抗原交叉呈递方面有效,使得CD4+和CD8+T细胞被血源性抗原激活。一旦活化,LSEC即分泌趋化因子CXCL9和CXCL10,并募集淋巴细胞。另一方面,LSEC能够表达由活化T细胞同源相互作用触发的PD-L1来消除这些T细胞。相反,暴露于源自KC的可溶性分子如IL-10和前列腺素E2(PGE2)可减少促进肝脏中免疫耐受的LSEC表面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
2
KC
KC占机体所有组织巨噬细胞的80-90%,占肝脏中非肝细胞的20%。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可能是成熟KC发育的关键因素。大KC主要位于门管区附近的肝腺区域,具有较高的溶酶体酶活性和更强的吞噬能力。大KC也产生TNF-α,PGE2,IL-10和IL-1,而中央静脉临近的小KC则产生高水平的NO。KC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将“自我”与“非我”颗粒区分开,具有APC和清除微生物的功能。一种识别“自我”和“非我”的分子是Dectin-2-先天免疫受体家族的C型凝集素受体,能够识别肿瘤细胞。Dectin-2一旦识别了肿瘤细胞,KC即增强抗肿瘤细胞的吞噬细胞活性,这有助于抑制肝转移。
3
HSC
80%的全身性维生素A以胞浆内脂滴的形式储存于HSC中。一旦被激活,HSC代谢为维生素A和全反式维甲酸,并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MF),产生细胞外基质并在肝纤维化和肝硬化中起主要作用。TNF-α,IL-6和TGF-β促进HSC的活化和增殖,从而产生不同的细胞外基质(ECM)组分,包括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和I型胶原。HSC由静息状态活化至促纤维化状态,引发HGF产生,这导致c-Met表达细胞招募,也有助于c-Met表达的肿瘤细胞增殖并防止细胞凋亡。此外,来自HSC的IL-8分泌有助于肿瘤血管生成,这促进了肝脏中转移瘤的生长。
4
肝细胞
肝细胞占所有肝细胞的80%。肝细胞表达低水平的MHCI类分子和共刺激分子。然而,在炎症条件下,某些肝细胞表达MHCII类分子并启动过继性免疫应答。肝细胞在HGF,脂多糖或细菌肝毒素刺激下产生IL-6。
肝脏中的循环免疫细胞
免疫稳态依赖于免疫系统对病原体的应答能力。肝脏中各种循环免疫细胞与居留肝细胞相互作用并调节肝脏以及外周部位的免疫应答。免疫细胞群存在于肝脏的不同位置。
1NK细胞
NK细胞仅是循环淋巴细胞的一小部分,但却占肝脏淋巴细胞的50%。人类肝脏含有两种NK细胞亚群:常规NK细胞和肝脏驻留型NK(lrNK)细胞。lrNK细胞包含两种非重叠NK细胞群:CD49a(整合素α1)+NK细胞和Eomeshi(主要是CD56bright和CXCR6+)NK细胞。EomeshiTbetloNK细胞占人类肝脏NK细胞的50%,驻留于窦间隙中。该NK细胞完全不存在于外周循环中。EomeshilrNK表达较少的人类靶标受体,这表明它们会识别非人类靶标,如细菌或细菌产物。相反,CD49a+NK细胞主要存在于薄壁组织中,并且表达MHCI类分子的细胞毒性效应分子和受体;因此,它们可能识别并杀死病毒感染的细胞或癌细胞。这些lrNK细胞具有抗特定抗原的免疫记忆。
2
NKT细胞
NKT细胞被自体或微生物脂质抗原,或通过Toll样受体(TLR)信号通路激活,是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之间的桥梁。激活后,NKT细胞迅速分泌促炎或抗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从而确定后续免疫或耐受的方向。表达特异性T细胞受体(TCR)的I型不变NKT细胞包含95%的肝NKT细胞,而表达不同TCR的II型NKT细胞却不足5%。NKT细胞识别非肽抗原靶标,如脂质和糖脂成分。它们被IL-12或通过NKG2D与其在靶细胞上的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被激活。NKT细胞在癌症中的作用颇具争议。在肝细胞癌(HCC)患者中,分泌Th2细胞因子的CD4+Vα24/Vβ11I型NKT细胞在肿瘤部位累积并抑制肿瘤特异性CD8+T细胞应答。
3
T细胞
正常的人肝脏驻留淋巴细胞由相对CD4+T细胞较多的CD8+T细胞组成。循环T细胞经过肝窦,可以与KC和LSEC相互作用。未成熟的树突状细胞(DC)可能摄取肝脏上表达的抗原,然后呈递给门静脉或次级淋巴组织聚集体中的CD4+和CD8+T细胞。另外,抗原可能由LSEC,KC或肝细胞原位呈递。肝脏T细胞抗原识别的结果可能诱导T细胞增殖或活化诱导的T细胞凋亡。抗原识别也可能导致免疫偏差至抑制或调节表型。
结果确定取决于T细胞相互作用分子(包括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MHCII类分子,VCAM1,B7家族的共刺激分子和CD95(FAS))扩展面板上调和表达。这些分子也可能改变细胞运输,启动和诱导耐受。
一般地,随着免疫调节性细胞因子(如IL-10和TGF-β)的产生,肝脏中的LSEC和许多DC呈递的抗原强烈偏向于诱导具有调节表型的CD4+T细胞,而全身激活的CD8+T细胞和初始CD8+T细胞易发生细胞凋亡。肝脏以抗原非依赖性方式隔绝活化的T细胞,这些细胞的高凋亡率说明,肝脏可能是全身性T细胞的“坟墓”。表达PD-1的活化抗原特异性T细胞与LSEC上的PD-L1相互作用产生耐受或凋亡。研究发现,活化的T细胞在肝脏中短暂存活。
色氨酸2,3-加二氧酶(TDO)主要在肝脏中表达。相反,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存在于许多组织,并由干扰素(IFN)-γ诱导。TDO和IDO负责色氨酸(TRP)的代谢。TRP的代谢物犬尿氨酸(Kyn)与T细胞上的芳香烃受体(AHR)结合以抑制其活性。效应T细胞对低TRP水平特别敏感。TRP局部消耗抑制T细胞增殖并诱导细胞死亡。研究表明,AHR活化诱导Treg细胞分化。
CTC与肝脏微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CTC可以通过肝动脉和门静脉进入肝脏。肝脏中的CTC会遭遇多种居留细胞群,这些细胞群可以在肝脏中发挥各种免疫功能。UM肝转移建立和进展的实际机制大多是推测性的。根据已发表的文献以及有限的经验,研究人员提出了肝脏转移性UM的两个阶段生长模型。
1微血管阶段
此阶段起始于窦间隙中肿瘤细胞停滞。存活的肿瘤细胞的最终归宿可以通过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确定。这些相互作用可导致肿瘤细胞死亡或肝脏中肿瘤生长。通过CTC簇阻断窦血管可导致血流短暂阻断和局部缺血,可能导致机械应力和变形相关创伤造成的肿瘤细胞破坏。此外,LSEC上的VCAM-1表达增加并捕获进入肝脏的黑色素瘤细胞。研究表明,黑素瘤细胞进入肝脏24小时内,LSEC上VCAM-1表达显着增加,抗体阻断VCAM-1后,肿瘤细胞和转移细胞微血管滞留减少。组织缺血会诱导局部释放NO和活性氧,并杀死肿瘤细胞。
LSEC和KC很可能是CTC在肝脏中遭遇的首个居留细胞。局部肿瘤杀伤KC可以消除肿瘤细胞。KC还可以激活其他固有免疫应答细胞,如NK细胞,NKT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NK细胞可通过分泌穿孔素/颗粒酶或通过CD95/CD95L通路介导抗肿瘤细胞毒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TNF-α,IL-8和CXCL10可以激活宿主杀肿瘤巨噬细胞,募集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宿主免疫细胞。
2
生长阶段
虽然有效的一线防御能够击败某些困在肝脏中的CTC,但局部炎症反应也可以促进肿瘤细胞粘附LSEC并随后导致肿瘤细胞跨内皮迁移,从而导致细胞毒性KC和NK细胞逃逸。KC或LSEC产生的IL-10可增强趋化因子受体CCR5表达,但是通过DC下调CCR7表达颗预防其归巢至次级淋巴组织。E-selectin,VCAM-1和ICAM-1在肿瘤细胞停滞和外渗入肝实质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E-selectin有利于肿瘤细胞渗出以及随后侵入肝实质。肿瘤细胞侵入异常窦外间隙会引发HSC和巨噬细胞进入肿瘤。这些巨噬细胞被IL-4和IL-13极化为表达精氨酸酶-1的M2型巨噬细胞。募集的HSC释放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MP),并增加胶原蛋白产物。这样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募集,细胞外基质组装和转换以及肿瘤细胞增殖。肿瘤细胞也产生VEGF以促进血管生成。肝细胞通过分泌促进HSC募集和活化的因子IGF-1和IGF-2促成纤维化和新血管形成。IGF-1也可以直接增强肿瘤细胞的生长。
除与肝脏中各种居留细胞相互作用外,MDSC还被招募到肿瘤部位以回应由肿瘤和/或驻留肝细胞释放的介质。MDSC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多形核MDSC(PMN-MDSC)和单核MDSC(M-MDSC)。在肿瘤部位,M-MDSC比PMN-MDSC更显着,M-MDSC迅速分化成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以增强肿瘤生长。MDSC产生免疫抑制细胞因子,如IL-10和TGF-β,并诱导Treg。随后,肿瘤细胞和宿主免疫应答之间的免疫平衡转换至逃逸(生长)阶段,将更多的血管内皮细胞募集到肿瘤部位并使肿瘤进一步血管化。最终,肿瘤的血管形成导致转移部位肿瘤快速增长。
最近,Coupland研究小组进行了晚期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组织标本中炎性细胞的显微研究。研究人员在肿瘤和周围组织中均观察到了CD3+T淋巴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转移性UM中CD8+T淋巴细胞数量“少”,主要见于肿瘤/正常肝界面处肿瘤周围。相反,黑素瘤内具有高血管周密度CD4+T淋巴细胞。没有进一步研究CD4+T细胞的特征;然而,这些CD4+T细胞可能是从外周循环募集的Treg细胞。此外,他们在转移性UM中观察到“不确定”形态的CD68+和CD+TAM,这表明存在致瘤性M2表型。肿瘤组织中缺乏PD-L1表达,而源自转移性UM的肿瘤浸润性T细胞难以在体外扩增。转移性UM细胞缺乏PD-L1表达和CD8+T细胞边缘化表明转移性UM中抗肿瘤免疫应答受损。
Grossniklaus等人提出肝转移的两种生长模式:“浸润性”和“结节性”。他们假设表达高水平c-Met或CXCR4的原发性UM细胞聚集于含有HGF和CXCL12的肝脏。这些转移性UM细胞具有CD+肿瘤干细胞样表型,根据肿瘤处于窦间隙(浸润性)或门静脉周围(结节性),分为浸润性或结节性生长模式。浸润生长模式表明窦间隙内细胞生长。结节生长模式主要包含去除而非浸润邻近肝细胞的肿瘤结节。浸润模式肝转移表明肿瘤中缺乏VEGF蛋白,但肿瘤细胞诱导单核细胞中MMP9表达,通过组织平面解剖并创建“伪窦间隙”。免疫系统在两种生长模式中发挥的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
文章编译自:MizueTerai,MichaelJ.Mastrangleo,TakamiSato.JCancerMetastasisTreat.Immunologicalaspectoftheliverandmetastaticuvealmelanoma.;3:-43.
推荐阅读
1.肿瘤免疫检查点治疗“拦路虎”之肿瘤微环境篇
2.着力规范、夯实基础,迎接肿瘤免疫治疗的中国元年
3.最新进展丨胃癌干细胞或将成为新的治疗靶点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