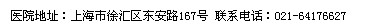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葡萄膜炎 > 葡萄膜炎饮食 > 综述丨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的治疗进展第
综述丨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的治疗进展第
作者:张慧平孙福成杨杰孚
国家医院心脏中心
本文章共计八个章节,将分期推出
一、TAVR患者的选择(第1期)
二、TAVR术的影像学评估(第1期)
三、TAVR的手术过程介绍(第2期)
四、TAVR的并发症(本期文章,分2期推送)
五、TAVR手术的效果
六、TAVR和经皮冠脉介入治疗的问题
七、瓣中瓣
八、TAVR的发展现状和展望
TAVR的并发症(2)
TAVR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与手术效果和预后直接相关,有的并发症为致命性,后果严重。
1.卒中
卒中是TAVR术的常见并发症,术后早期卒中和短暂性缺血发作(TIA)的发生率高于外科换瓣术后。SAPIEN瓣膜置入后30天内卒中发生率约为2%~6%,CoreValve瓣膜置入后30天内卒中的发生率约为2%~5%。约25%~50%的卒中发生在术后24小时内,80%的卒中发生于术后5天内。卒中或TIA多与来自主动脉瓣的钙化碎屑脱落或主动脉弓处的动脉硬化斑块脱落有关。导丝通过瓣膜、球囊预扩张、大尺寸的半僵硬瓣膜装置通过主动脉弓、瓣膜在瓣环中的定位、瓣膜释放后对原瓣膜的挤压、瓣膜的反复定位、操作时间过长,都是潜在引起栓塞的根源。另外,TAVR患者多为高龄,Af发生率高,也可能与术后发生卒中有关。
实际上,几乎所有TAVR患者在术中都会出现经颅多普勒(TCD)检出的异常信号,而术后行核磁共振检查,有68%~91%的患者有新发的无症状病灶。研究表明,经股动脉和经心尖途径置入SAPIEN瓣膜,TCD记录到的一过性高密度信号(HITS)数量相似,尽管经心尖可避免经过主动脉途径,但优势并不明显。球囊预扩张本身增加的微栓塞并不多,但扩张破坏了血管和瓣膜的保护性内皮层,使易碎裂组织暴露,后续瓣膜定位和释放过程中的微栓塞明显增多。因此有术者认为,瓣膜置入前不行预扩张是合理的。由于CoreValve瓣膜的定位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而SAPIEN瓣膜的精确定位颇为费时,因此后者在置入过程中记录到的HITS信号明显多于前者;而在瓣膜的释放过程中,SPAIEN瓣膜是球囊快速加压一次性释放,而自膨式CoreValve瓣膜是自身逐步缓慢释放,与原钙化的瓣叶组织刮擦明显,导致释放过程中的HITS信号明显增多。通常,瓣膜释放后的后扩张并不引起更多的HITS。
尽管大部分患者影像学能记录到微栓塞的征像,但只有少数患者临床诊断卒中。无症状性微栓塞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有关,卒中则明显增加死亡率。在PARTNER研究中,TAVR术后发生严重卒中(改良RankinScale评分≥2)患者的1年死亡率高达66.7%,而无严重卒中患者为27.7%(P0.)。减少微栓塞和卒中的发生重在预防,技术操作要熟练、避免在钙化的瓣膜上过度操作、在无名动脉和左颈总动脉处使用保护装置等。设计创伤性更小的瓣膜装置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2.心律失常:
(1)术前发现的心律失常与术后发生心律失常的关系
严重AS患者多为高龄,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慢性心功能不全,左束支传导阻滞(leftbundle-branchblock,LBBB)或严重心动过缓的发生率高。在Urena等的研究里,术前无心律失常史的AS患者中,有16.1%的患者有经24心电遥测记录到的新发心律失常,包括阵发Af或房性心动过速(atrialtachycardia,AT)、间断LBBB、高度房室传导阻滞(atrioventricularblock,AVB)或严重心动过缓及室性心律失常。术前发现的新发心律失常与TAVR术后出现的心律失常密切相关。在Urena的研究中,术后发生Af、AT及需要行永久起搏器植入的患者,有约30%在术前就有未引起注意的阵发Af或AT及严重缓慢型心律失常;而术前有阵发Af或AT及严重缓慢型心律失常的患者有约一半术后发生持续性Af、AT或需要接受永久起搏器植入。术后出现持续性LBBB的患者中,有近10%术前即存在间断性LBBB,而术前记录到间断性LBBB的患者几乎全部会在术后出现持续性LBBB。术前新发现心律失常的患者有43%在术后治疗方案上作了相应调整。
(2)TAVR术后的Af等快速性心律失常
TAVR术后新发Af的发生率约为10%~30%。TAVR术后出现Af等快速心律失常的可能原因有:①严重AS患者大多有左室压力负荷慢性增加,致左室肥厚和左房负荷增加,长期出现左心功能异常,Af和室性心动过速(VT)的发生率均明显增加;②经心尖途径的TAVR术由于胸廓和心包被切开,心脏局部组织在愈合过程中局部炎性反应,会增加Af的发生率。新发Af可以为阵发性,发作时间短,多小于1小时。由于新发Af多未进行抗凝治疗,因此TAVR术后新发Af患者的脑卒中发生率增加更显著。
(3)TAVR术后左束支传导阻滞和缓慢型心律失常
TAVR术后新发LBBB的发生率约11%~65%。电生理研究发现,AS患者易有A-H、H-V间期延长,TAVR术后易发生QRS波延长;术前QRS波较宽反映了传导系统本身就存在退行性变,这类患者术后易出现LBBB。在Khawaja等的研究中,术前P-R间期延长及AVB,与术后发展为高度AVB相关。TAVR术后出现的LBBB和高度AVB,与猝死等心脏不良事件有关。
注:VAJ(ventriculoarterialjunction)—室房结合区;VS(ventricularseptum)—室间隔;MV(mitralvalve)—二尖瓣;LBB(leftbundlebranch)—左束支;MS(membranousseptum)—室间隔膜部;RFT(rightfibroustrigone)—右纤维三角;N代表无冠瓣;L代表左冠班瓣;R代表右冠瓣;STJ(sinutubularjunction)—窦管结合区;LFT(leftfibroustrigone)—左纤维三角
TAVR术后发生LBBB或高度AVB等缓慢型心律失常的原因与主动脉瓣的局部解剖结构有关。钙化的主动脉瓣与包括房室结在内的传导系统毗邻,紧邻的希氏束在瓣膜的置入过程中尤易受到损伤。左束支位于室间隔膜部的最上方,与主动脉瓣环紧靠,从由无冠瓣、右冠瓣和右纤维三角(二尖瓣叶向主动脉瓣折返,朝向室间隔膜部的增厚部分)构成的叶间三角间底部发出。正常的主动脉瓣三个瓣叶呈半月形附着于瓣环,瓣膜边缘距传导系统较远;而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瓣叶融合成环形,向室房交界区(瓣环)挛缩,瓣叶与左束支距离变近,当右冠瓣和无冠瓣明显融合时,这一点尤为突出(图A、B)。CoreValve瓣膜的长裙式部分恰定位于室房交界区(瓣环),瓣膜扩张后支架的径向作用力与钙化、欠规则的瓣环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到临近组织,因此,瓣膜装置在主动脉根部的精确定位直接关系到与左束支距离的远近(图C)。CoreValve瓣膜裙式部分的植入深度和自身残余瓣膜组织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瓣膜装置与左束支的距离。CoreValve瓣膜较SPAIEN可扩张瓣膜置入后LBBB的发生率要高,甚至可高达4倍,即与自膨式瓣膜支架的裙式部分在左室流出道的置入位置较深有关,而爱德华的SPAIEN瓣膜较短,距离左束支相对较远。在Piazza的研究中,CoreValve瓣膜在左室流出道的置入深度如果6.7mm,则术后无患者发生LBBB。
在操纵导管、硬导丝、瓣膜预扩张和后扩张的过程中,左束支易受到机械性损伤,大部分患者术中即出现LBBB,但有5%的患者为术后发生LBBB。有尸检报道,在SPAIEN瓣膜置入后,室间隔基底部发生了局部缺血性坏死,并波及到了局部纤维传导系统。损伤主要是受一过性炎症、水肿、缺血或机械应力的影响,自膨式瓣膜置入后出现的LBBB约1/2在1月内逐渐恢复,可扩张瓣膜术后的LBBB约1/3在1月内恢复。在Urena等的另一项研究中,接受可扩张瓣膜支架置入的名患者,术后有高达61名(30.2%)出现了LBBB,但出院时有23名(37.7%)完全恢复。从心尖入置入SAPIEN瓣膜时,由于避免了弯曲硬导丝在左室内的操作,LBBB的发生机率要低。令人困扰的是:TAVR术后出现的LBBB是否会进展为高度或完全AVB;即使不发展为AVB,持续存在的LBBB使两心室运动不同步,长期必将对心功能造成不良影响,心功能受累后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增加,这些都与预后不良有关。
(4)TAVR术后的起搏器植入
TAVR术后因缓慢性心律失常需接受永久起搏器植入的比例约为10%。CoreValve瓣膜置入后起搏器植入的比率约为30%,而EdwardsSPaiens瓣膜置入术后约为6%。有人把TAVR术后出现的起搏器植入需求,看作是这种技术应用后的一种必然。上述Urena的研究中,出院时仍存在LBBB与晕厥、完全AVB和永久起搏器植入的需求明显相关(20%vs.0.7%),出院时仍有LBBB的患者基本上每5个人在后续的随访期间有1人接受了永久起搏器植入,术后新发LBBB是起搏器植入唯一的预测因素,1年随访时仍有LBBB者左室射血分数(LVEF)下降(4.75±8.02)%(69)。在Houthuizen等的研究中,TAVR术后出现LBBB的患者1年全因死亡增加近60%(37.8%vs.24.0%,HR1.55,95%CI:1.17~2.06),TAVR导致的LBBB是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73)。对于术前即存在的右束支传导阻滞(rightbundle-branchblock,RBBB),也有研究表明其与TAVR术后的起搏器植入需求相关。在Khawaja等的研究中,术前存在RBBB的患者术后接受起搏器植入的机率最高,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RBB已存在阻滞,一旦LBB再出现阻滞,即会进展为完全AVB。Khawaja等还发现,TAVR术后出现AVB、QRS波增宽、瓣膜置入前的球囊预扩张、室间隔直径增宽、使用29mm的瓣膜与TAVR术后起搏器的植入需求独立相关,如果术后出现束支传导阻滞,需要严格观察至少5天,以防进展为高度AVB。对于TAVR术后出现的新发LBBB,如果心功能改善不明显甚至有恶化的患者,可考虑心脏再同步化治疗。
3.感染性心内膜炎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endocarditis,IE)是TAVR的少见并发症,发生率约为0.1%~3.03%。在血管和心腔内的操作是感染发生的基础,瓣膜装置的金属骨架结构和附着其上的瓣叶成为感染的基质。瓣膜塑形和预置过程中,造成的瓣叶损伤增加了发生IE的可能。瓣叶和金属骨架结构、二尖瓣、升主动脉是感染的好发部位,偶尔可形成升主动脉-左房或右房瘘,极少数患者三尖瓣也会受累。大部分患者有赘生物形成,主要位于所植入瓣膜的瓣叶、骨架结构和二尖瓣。在Amat-Santos等的研究中,TAVR术后发生IE的中位时间是6个月,气管插管和使用自膨胀式瓣膜是发生IE的独立危险因素。气管插管会导致菌血症,接受TAVR的老年患者尤易出现。自膨胀式瓣膜较可扩张式瓣膜术后发生IE的风险升高2倍,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两种瓣膜的不同设计和植入前塑形、预置,以及操作过程有关。自膨胀式瓣膜尺寸较大,与自主瓣叶的接触面积较广,似乎有利于细菌的附着和播散。TAVR相关IE的病原学以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和肠球菌为主。接受TAVR术的患者常合并多种内科疾病,身体状况差,发生IE后发热等症状不典型,约20%的患者表现为乏力、体重下降,少数患者还会以卒中为首发表现。新出现的心脏反流性杂音通常认为是IE的重要体征,但相当一部分的患者在术后本身即存在残余瓣周漏或二尖瓣关闭不全,给IE诊断带来困难。发生IE后的主动脉瓣反流可以是新出现的,也可能是原有反流加重,部分患者还会有植入瓣膜的早期退行性变,瓣膜上局部血栓形成,瓣膜跨瓣压增大。
接受TAVR术的患者发生IE后常会有心功能失代偿,心衰恶化。研究表明,合并心衰和感染性休克后住院死亡率可达45%,1年死亡率高达66%。除了抗生素治疗,对于不能控制的感染,应考虑外科移除瓣膜,但手术难度大、风险高,对于附着于升主动脉的自膨式瓣膜,尤其困难。在接受充分抗生素治疗后,复查血培养阴性,确认感染已控制的患者,如果仍存在严重主动脉瓣反流,而患者有心衰或无法行外科手术,可考虑再次植入一人工瓣膜(瓣中瓣)。
白癜风有妙方北京那家医院治疗白癜风好啊